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之后,冷战结束。最近一、二十年,冷战时期设计研究一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2008年,英国V&A博物馆举办了题为“冷战摩登:设计1945-1970”(Cold War Modern Modern: Design 1945-70) 的展览,后来关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设计展也多了起来。比如,鹿特丹美术馆2015年举办的“红色财富:苏联设计1950-1980”(Red Wealth: Soviet Design 1950-1980)、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2018年举办的“水泥乌托邦:南斯拉夫建筑展”(Toward a Concrete Utopia: Architecture in Yugoslavia)以及杭州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2022年举办的“从呼捷马斯到未来图景——苏俄设计历史”等。为纪念中德建交50周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联合德国维特拉设计博物馆等机构特别策划举办了“交织的轨迹——德国现代设计1945-1990”大展。这个展览非常重要,因为德国在二战之后被分成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德是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矛盾对峙的前沿和焦点。而这个展览所聚焦的,正是冷战期间的两德设计,展览的视角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二战后的设计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就二战之后的德国谈二战之后的德国设计,其实是谈不清楚的。因为从1945年德国战败投降到1990年两德统一,这只是一个比较短的历史时间段。从设计和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要放在一个较长的“中时段”,也就是在一、两百年的时间里来观察和讨论,可能才能看得更为清晰。从“中时段”和现代文明的进程来看,对德国设计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有两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这两个大的背景,对于英、法、德、美等都是一样的,具体而言又不相同。比如英国是启蒙思想的重要起源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角,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参与与其他国家相比就显得比较少。法国是启蒙思想的主场,也深度参与了两次工业革命,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巴黎从17世纪开始成为欧洲艺术的中心,不光是纯艺术的中心,在实用美术、装饰艺术领域,巴黎也是中心。影响美国设计的主要是两次大革命,工业革命和美国大革命,美国大革命也是启蒙运动的后果。
德国现代设计的发展也有自身的特点,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不能忽略:其一,从启蒙运动来讲,就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这奠定了德国人理性、系统的思维方式。二战两德分裂之后,一边所实行的是美国化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德国的系统设计思维经历了经验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洗礼;另一边所实行的是苏联化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物,所反映出来的也是一种系统设计思维。其二,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设计主要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后果。这个展览所聚焦的,总体上来说仍旧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后果,后面的设计有一点信息革命影响下的设计,但是比较少。工业革命不只是技术革命,而是以核心技术的突破为标志,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上层建筑,引发的一系列制度、路径和思想上的变革,所以,工业革命本身就是一套系统和体系。

毫无疑问,“系统”及其所延伸出来的系统思维、系统设计、系统论,是德国设计的关键词。所以,在这里,我们想紧紧围绕“系统”这个概念来谈一谈我们的思考。主要谈三点:
我们在设计里面讲“系统”和“系统论”,它在哲学里面所对应的就是“体系”这个概念。海德格尔曾经对“体系”的概念和历史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体系”希腊语的原意为“我来安排”,它有两个意义指向:其一,是内在的、给事情提供其根据与支点的结构;其二,是外在的随意的堆积框架。后来,“体系”这个概念被用在认识论的领域,由于“体系”这个概念本来就含有这两种意义指向,这使得人们一方面努力创造真正的哲学体系,另一方面也把随意堆积起来的一些随感以“体系”的名义招摇。海德格尔认为古希腊、中世纪都没有严格意思上的哲学体系,真正的体系是在17、18世纪形成的,因为直到近代“体系”才具备了它形成的必要条件,最重要的就是数学的理性体系在人类思维中占据优势统治地位。而在17-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变迁的过程中,“体系”是“整个哲学的主导词语”。
伏尔泰在《百科全书》里解释“体系”这个概念说,世界上有三种体系:其一,是讲一般的或抽象原理的“抽象体系”;其二,是建立在一些列假说之上的“假说”;其三,是由在实验中收集并经过考察和鉴别的事实做构成的体系。海德格尔说:“体系一般的首先并非是、也并非仅仅是给现有知识材料和值得知识的以一种次序,以期适当传达知识,反之体系是可知东西本身内在的安排,是给其以论证性的形态和展示,更真切的说,体系是对存在东西在其存在东西性内结构与衔合的合知识性的安排。”也就是说,体系是一种内在的合乎理性的结构秩序。所以,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是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论传统,也就是伏尔泰说的第一种“抽象体系”。马克思主义用唯物论把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论传统颠倒过来,加上辩证法变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但是他的思维的基础也是德国哲学家所追求的这种体系哲学。
英国设计史家杰里米·安斯利(Jeremy Aynsley)的《设计现代德国》(Designing Modern Germany,2009)是较早将两个德国的设计放在一起进行观察的著作。他发现,德国分裂之后,尽管民主德国的政治局势复杂且不断变化,但民主德国的设计师事实上一直致力于寻求与联邦德国的相似之处,并渴望与联邦德国的同行拥有相似的设计原则和理念,比如标准化、功能主义、优良设计、系统设计等在德国所确立的设计现代性的主张。我想,两德设计之所以能够在不同的设计会制度条件下“求同”,除了他们所共享的现代主义设计的原则和基础,更为根本的还是德国古典哲学所确立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说,德国的现代设计,他的系统设计的理论就根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体系哲学的思维方式。事实上,瓦格纳的所谓“整体艺术论”以及包豪斯把建筑这种综合性的艺术作为最终目标的追求,可以说都是根源于德国哲学注重体系的思维方式。二战之后,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仍旧对联邦德国的设计思考起到重要影响,而民主德国的设计所遵从的事实上是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思想基础仍旧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德国古典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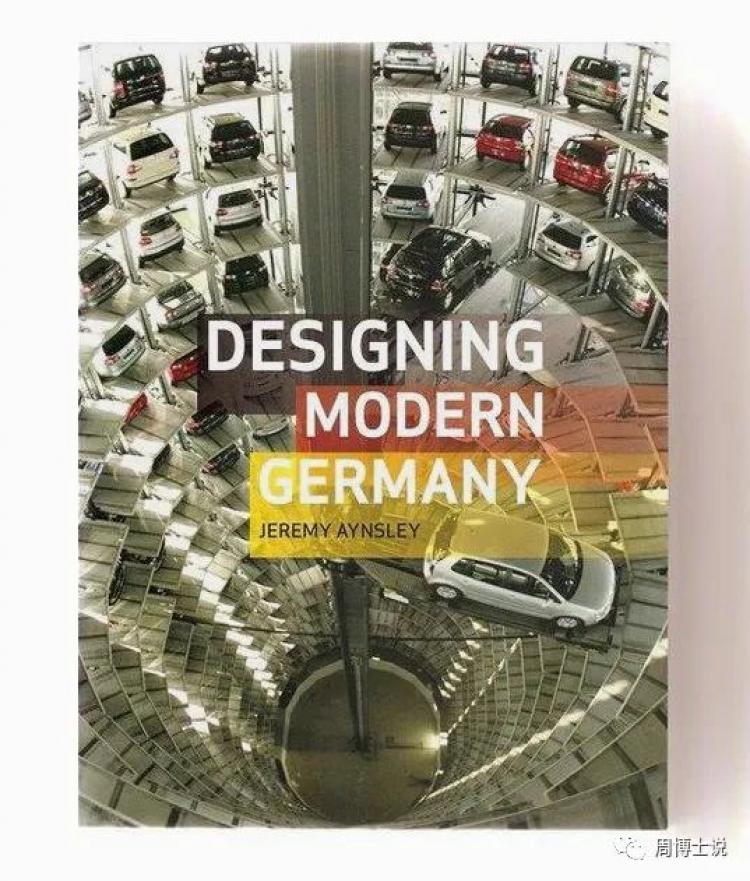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德的设计师都在理性的基础上寻找问题的原点和解决之道,构建设计的理念和方法论系统,树立标准和实施规范,这种相似的系统论思维正是德国体系哲学这个大的思想传统在两德设计思想上的反应。
德国设计的崛起,主要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密切相关。德国基本上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但是德国深度参与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60、70年代,到20世纪中期达到顶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包括,首先是电气化,也就电力的广泛使用。而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德国工程师西门子于1866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大功率发电机。其次,是内燃机的发明和新型交通工具的创制,比如汽车、轮船、飞机等,它们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汽车。汽车的技术和工艺,成为机器时代的艺术和设计的原型。1866年,德国工程师尼古拉斯·奥托发明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立式四冲程内燃机。1876年,又试制出第一台实用的活塞式四冲程煤气内燃机,这台内燃机被称为奥托内燃机,为汽车的发明奠定了基础。1886年,卡尔•本茨为其在1885年研制成功的三轮汽车申请专利,这标志着汽车的诞生。同年,德国人哥德利普•戴姆勒制成世界上第一辆四轮汽车。1887年,卡尔•本茨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汽车制造公司——奔驰汽车公司。随后,法国、美国、英国等相继成立了许多重要的汽车公司,而德国的汽车工业则直到今天仍旧在全球的汽车制造业中遥遥领先,这便是德国产业界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所致。

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德国设计”或“德国制造”,其实具有一种像靶子一样的同心圆结构,其核心是电力和能源革命,围绕核心的第一圈是包括内燃机、无线电通讯等在内的各种技术发明创造,向外拓展就是以这些技术和发明创造为基础的各种生活用品,比如电灯、电话、收音机、汽车、飞机等等,再往外就是企业制度和工业设计。这是一个以技术为基础,围绕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展开的高度自足的系统,这个系统在思想、方法和实践上不断完善,就成就了所谓“德国制造”。我们在现代设计史上所讲到的,以德意志制造联盟、包豪斯和乌尔姆设计学院为代表的德国设计、德国制造和德国设计教育,其实都是顺应工业时代的要求,调整设计发展的大方向,勇立潮头、主动作为的产物。但是,在以信息化作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德国则明显的落后于美国,美国成为当仁不让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巨无霸。这使得德国在工业划时代所养成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在数字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荡然无存,而美国的互联网巨头则纷纷通过购买、参股等各种方式涉足欧洲具有优势的制造业领域,这使德国感受到了来自美国互联网资本的巨大威胁。所以,德国提出工业4.0并视之为国家战略,其实就是想努力实现实体的工业生产,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与虚拟数字信息世界的无缝对接,从而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浪潮,使德国的工业企业继续在全球的技术和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本次展览“交织的轨迹:德国设计1945-1990”截止于两德统一1990年。此前一年,英国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了互联网,信息时代到来。所以,这个展览事实上划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历史单元,在这段时间里“德国制造”以其高水平的设计和高质量的品质成为全球工业化制成品的标杆,德国人对他们的设计和工业制成品极为自信,这个建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基础上设计系统日益完备,然后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系统因为日趋完善而走向封闭,其实是真正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同时期的日本事实上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尼葛洛庞帝在他的名著《数字化生存》中就曾经提到过传统制造业的这种匠人意识和尾大不掉,以及因为抓不住新时代的契机而与新发展的可能性失之交臂的故事。这个问题在德国制造业中事实上也是存在的,否则也不会有后来的德国工业4.0。


3、工具理性与个体
如果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我们会发现,17、18世纪所形成的德国的体系哲学,天然的适合工业化、现代化和机器时代,或者说它们是同构的,因为都以数学作为理性思考的基础。在这样一个日趋严密的系统中,工具理性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人就越发的容易变成工具,人的想象和批判性的反思就会变得不那么容易。试想,为什么是如此强调理性的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而设计界对于工具理性的困扰和担忧,事实上在1914年德意志制造同盟著名的“科隆论战”中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当时,代表官方立场的穆特休斯和以艺术创造为本位的范德维尔德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大致概括为七个方面:标准化——个性化;统一性——多样性;规范——自由;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理想主义;以出口为目标——以自主创造为根本。在穆特休斯的逻辑中,设计师、艺术家个体要服从于德国的工业化和世界贸易竞争这个大的系统框架,艺术家和设计师的职业追求也要以标准化为目标,个体的创造只是这个国家利益和产业竞争这个大系统里面的一个要素。所以,德国的现代设计在他发端的时候就极为强调设计的“工具理性”的层面,属于价值理性的那些更为注重艺术和文化,更加个性化的和情感化的表达,在技术发展和产业竞争的大格局中事实上是逐渐式微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和拉扯,在一战之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与包豪斯又伴随始终。


与之相关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德国艺术和设计的关系问题(格罗皮乌斯在Ulm设计学院揭幕演讲中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在法国、意大利,甚至同为新教国家的荷兰都不是问题。但是在德国就很不一样,德国的现代设计似乎一直有一种明确的倾向,就是要拉开设计与艺术的距离。因为艺术非常强调个体的观点、创造力和价值,而这与德国设计所推崇的工具理性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在一战之后,对这种看似理性、系统的思维方式展批判最为猛烈的也是艺术家。德国的达达艺术所主张的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反体系、反秩序,他们反对看似正确的国家主义逻辑,反对军国主义对人性的蛊惑、奴役,对生命的摧残。对于德国的政治和产业来说,我们可以说德国设计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也可以说它是是既有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顺民,设计这个小的系统自然要服从政治、经济和产业的大系统,这样一种系统论自然是排斥个性、感性和反叛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与英、美、法等国的设计届不同,德国的设计界对于塑造设计明星并不热衷,他们更相信系统的力量。联邦德国如此,强调集体主义的民主德国更是这样,两德统一之后也没有多大变化。
然而,设计创意,如果没有个体对于系统的突破,没有个体对于墨守成规的抗议,其实是暗淡无光的。好在德国设计,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德国人的设计,而是德国人和在德国工作的人的设计的一个统称。比利时人范德维尔德的争论、包豪斯以及乌尔姆多元化的国际教员构成都表明,德国设计还有一个国际化、开放的面向,这使得德国设计界在系统设计之外还保有革新的可能。
所以,当我们看到后现代的德国设计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鲜活的设计理念蕴含着许多不同于德国体系哲学的来源。比如,弗兰克·施莱纳(Frank Schreiner)领导的西柏林史提雷托工作室(Stiletto studios)设计的《消费者休息椅》等系列作品,通过工艺的细微调整和概念化,将消费社会中的现成品变成了一件颇具幽默感的家具。弗兰克·施莱纳的作品发展了杜尚的智慧,而他后来确实也变成了一个艺术家。再如,没有受过正规设计教育的英格·毛雷尔(Ingo Maurer),他的灯具设计充满了超现实主义和诗意的特征,显得很不德国。为什么会这样呢?应该说与他的国际化经历有关。在美国的生活经历让英格·毛雷尔感受到“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与德国相对保守的思维模式相比,美国人总能对我的奇思异想做出鼓励和肯定的回答,开放的态度坚定了我走自己路线的决心。”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些德国的后现代作品时,我们会有一种惊讶又放松之感。这不是德国的吧,这怎么可能是德国的?!可这就是德国的。

▲ 消费者的休息 弗兰克·施莱纳
 ▲ “哔哔哔哔”台灯 英戈·毛雷尔
▲ “哔哔哔哔”台灯 英戈·毛雷尔虽说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更为艺术化、更强调个体和异想天开的东西在德国设计系统中更像是一个异数。但是这种追求标新立异、突出个体和想象力的思想一支潜藏在德国设计的深处,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一些令人惊讶的人。比如,在时尚设计领域还有一个来自汉堡的“老佛爷”拉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按照那种对于德国设计的死板看法,“老佛爷”的设计就更加没法归类了,其实他设计思考的内在有许多很德国的东西。当然,以功能主义和优良设计为基础的系统设计在德国根深蒂固,仍旧并行不悖的发展着,它以功能主义为基础,又加上了绿色和可持续设计的原则,融入了更多的跨学科的要求。这些仍旧构成我们今天对于“德国设计”的一般看法,不过,在这些系统性的建构之外,我们仍旧要关注那些独特的、充满张力的个体。
卓别林的电影《大独裁者》(1940)末尾的台词说道:“我们发展了速度,却隔离了自己;机器本应创造财富,却使得我们更加穷困;我们拥有了知识,却变得愤世嫉俗。我们变得聪明、伪善和冷漠。我们思考太多,感受太少。比起机器,我们更需要人性。比起精明,我们更需要善良与温情。没有这些品质,生活会充满暴力和迷茫。”这段话可以批判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人,事实上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德国设计的系统论。
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当一个诞生原创的系统高度完善之后,它很可能就会走向原创的反面,给革命性的可能关上了大门。一个封闭且日益完善的系统一定是创新的敌人。所以,系统,本质上与可能性的问题相关。越是在一个看似合理的系统中,可能越是要对理性的执迷保持警醒。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是:在系统之外,在系统的边缘,设计的还有什么可能?可能,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可能可能。
(原刊于《艺术与设计》2023年第3期)
